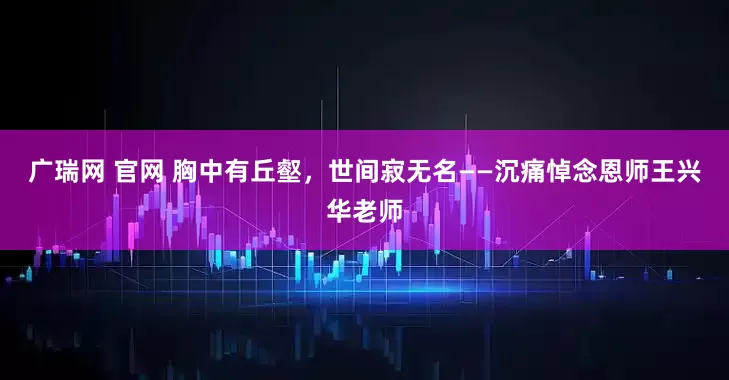
一、“王兴华老人”
王兴华老师去世了。噩耗来得很突然,使人猝不及防。尽管我们都知道“人固有一死”,但噩耗仍然让我肝肠寸断,悲痛欲绝。王老师的离去对他个人也许是种解脱,也使他能早日与逝去的亲人团聚,但对我们来说,导师的去世却是难以弥补的伤痛,从此刻开始,我们少了一个牵挂的人,却多了一份深重的孤独感。而且王老师不是“名人”,他的告别仪式可谓“极简”,不但去掉了一切世俗的“雕饰”(如遗像、挽联、花圈、生平介绍等),连称呼也只是“王兴华老人”。对此悲观地看,那就是“生前寂寞,身后凄凉”,而达观地看,那就是“圣人无名”!王老师胸有丘壑,却寂寂无名,这不正是庄子所孜孜以求的生命境界吗?虽说如此,那天、那个简陋的殡仪馆、那个房间的景象,仍然使我心中郁结,难以释怀。说实话,如果任由王老师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,那是我们这些为人弟子者的耻辱。
二、生机勃勃的南开园
我与王老师的缘分始于1986年。那一年,我考上了南开大学美学专业的研究生,9月份我踏入了南开校园,开始了我梦幻一般的研究生生涯。在南开之前,我虽然已经读了很多美学书和哲学书,但我真正进入美学和哲学之门还是在南开。在南开哲学系,有许多知名的哲学家,如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温公颐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晏清、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学家方克立、西方哲学史学家车铭洲和冒从虎、逻辑学家崔清田等,他们对我后来的发展都有很深的影响,尤其是方克立先生。

南开的美学学科,那时刚刚建立,导师只有童坦和王兴华两位老师。童老师研究美学原理,王老师主攻中国美学史,两人共同开创了南开的美学学科。当时的南开园,生机勃勃,学风浓厚,思想和学术活力充盈,到处是一派自由开放的气象。那时的我们,对真正的学术一知半解,但思想活跃而理性不足,充满热情而不乏激进,但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南开大学都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我们。那时,“尼采热”刚刚兴起,《天津日报》记者来采访研究生如何看尼采,我们几个美学专业的同学就尼采侃侃而谈,我后来每每想起都觉得“颇为幼稚”,但当时《天津日报》竟然登了出来。也是在那时,齐鲁书社首次出版了全本的《金瓶梅》,美学专业的研究生有幸得到了5本,我把自己的那一本转让了出去,但也因此使我“有勇气”在南开举办了关于《金瓶梅》的“讲座”,想起来还是觉得“幼稚”。童老师、王老师对我们的“幼稚”心知肚明,但都报以宽容的微笑,鼓励我们继续思想和学术的探索。
三、“审美与艺术的心灵”
那一年的南开美学共有8位同学,在南开美学专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。分导师的时候,朱爱军、顾弘镔、汪建新选择了童老师,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,最终选择了王老师。之所以犹豫,是因为在“原理”和“历史”之间的难以取舍,我那时对“理论探索”充满兴趣,但又自觉有一种“历史感”,故有此“犹豫”,现在想来就是一种生命的“因缘”所致。王老师性格方正,风骨清峻,然而内心充满激情和想象,感性的生命力和理性的精神力统一在一个鲜活的生命整体中。他热爱艺术,善书法、绘画、摄影,书法字体优美,法度谨严,又不失深情和灵动之势,山水画则山石嶙峋,树木森然,气势雄浑邈远,摄影我不懂,只记得他对黑白摄影评价极高。终其一生,王老师都保持了一颗“审美与艺术之心”,这是他历经患难而热爱生活的力量源泉之所在,也是他醉心于中国美学研究的动力之一。王老师常说,“治美学者必须至少通一艺”,此论虽不必然,但他自己确实做到了,他的美学研究就是以深厚的艺术功底为支撑的。所以,王老师特别重视美学专业的艺术训练,他带我们去看江南园林,去北京看原版苏联电影,都旨在增强我们对艺术的审美感知和艺术品鉴能力。在这一点上我很惭愧,我平生虽热爱艺术,然而对于绘画、雕塑、音乐、戏剧、电影等各种艺术都无“实际创作经验”,唯在写诗上有少许心得,当年也选修了南开中文系的“诗歌美学”课。聊以自慰的是,受王老师影响,我至今仍保持着一颗“审美与艺术之心”,这也是我在艰难困顿之时仍然能自由而不沉沦的原因。

四、 耕耘在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的田野上
但王老师不仅是个艺术家,而且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。王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,又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,进入南开后先后在马列教研室、政治经济系任教,于1962年参与哲学系的复建工作,一直在哲学系工作到退休。王老师对中国哲学有深入的研究,80年代曾参与了萧萐父、李锦全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的编写。此书在当时是一部全新的中国哲学史教材,它去除了此前同类著作中的“左”的痕迹,从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规律出发,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历史统一的观点,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和各个时代著名哲学家的思想,在80年代影响很大,我也从中受益匪浅。王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他参加编写时的一些故事,至今印象深刻。但王老师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美学领域,主要著作有《中国美学论稿》、《中国哲学史》(合著)等,任《中国历代美学文库·先秦卷》主编、《中国哲学大词典》编委,曾任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、天津美学学会副会长、国际中国哲学会会员。
作为南开美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,经过长期的艰苦思考和学术工作,王老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美学思想和中国美学史观。他认为,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,审美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份,是人们悦乐身心,自我完善,并按照理想和美的规律创造和选择文化的过程。美学研究必须坚持和深化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,不能脱离审美和艺术的实际去进行贫困的玄思,更不应以晦涩繁琐的文字堆砌去建构体系。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创造中,积累了丰富的审美经验、艺术才华和博大精深的美学思想,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智慧的表现。中华民族又是主张平等、富于自由精神的伟大民族,但在特殊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,这种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往往与对自然的热爱融汇在一起,“自然”成了中国人的“自由的理想和美的观念”。他在《中国美学史论稿》“序”中说:“中国人最高的人生境界既是哲学的,又是审美的。中国艺术的极致总是蕴含着深邃的哲理。哲学的本体论、认识论、伦理观念和美学有着内在的、不可分割的联系。这样,感性与理性,艺术和哲学,审美与人生便历史地在实践中不断统一起来,从而形成中华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。在运流更迭,历经变乱的历史长河中,每当理性精神的兴起,总是伴随着‘审美和艺术的自觉’。”他的中国美学史研究,就是致力于揭示中国人的“自由的理想和美的观念”,揭示中华民族“审美和艺术的自觉”。他熟悉中国美学史料,尤其是文论、诗论、画论等,他坚持从史料出发,对史料做义理分析和艺术分析,故能自出机杼,不落俗套。90年代,他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美学“意境论”,发表了《中国美学“意境论”新探》、《意境与审美空间的营造──中国美学“意境论”新探之二》等,对“意境论”做了深刻的阐释,他特别从诗歌、绘画和园林艺术的时空境象出发,对“意境论”与“空间境象”之间关系的阐释,超迈前人,最能显示其才华与卓思。今日很多人热衷于谈论的“审美空间的营造”,王老师在30多年前就谈过了。
五、教书育人的无量功德
王老师毕生的事业就是教书育人。他带了多少本科生我不知道,研究生从84级开始,共有10多人,皆事业有成。我们那一届有杨岚、武菲、周成名、高锐涵和我5个人,杨岚、周成名和我在高校工作,高锐涵在深圳从事实业,武菲在国外生活。杨岚是南开大学教授,主要从事美学研究,著有《人类情感论》、《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》等。周成名是温州商学院教授,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,是湖南省第一位经济学博士,著有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》等著作。我毕业后一直在云南师范大学工作,199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,师从方克立先生,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和佛学,但也涉猎历史学、文学、政治学、法学等学科,著有《心识的力量——太虚唯识学思想研究》和《佛法与自由》等,担任过中国哲学、逻辑学、美学、宗教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和法学等多个专业的研究生导师。
我们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,固然是个人奋斗的结果,但与南开的培养和王老师的教导有方有不解之缘。王老师的性格可以用“温而厉”来形容,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,但又从来没有过“严厉批评”,即使我们偶尔犯错,他也总是委婉地予以提示和点醒,促使我们自己反思和改正。在美学思想上,我那时受李泽厚影响特别深,对蔡仪先生的美学思想比较排斥,王老师教我看蔡仪一派的长处,学会兼容并包。在教学实践上,他安排我和杨岚承担本科生的“美学”课,并悉心指导我们上好课。在科研训练上,王老师也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,因材施教,善巧方便地予以培养。1987年,他带我们集体出席了在南通召开的全国美学会议,我们在一起讨论到当时的美学教材和美学教学,他鼓励我撰写了《高等学校美学教学问题》一文,又和我一起讨论,删掉其中激烈批评的文字,最后以“南开大学美学研究生”的集体名义发表。1989年,方克立先生发起《中国哲学大辞典》的编写,王老师任编委,他和我一起商定美学部分的词条,分配我承担了一半词条的撰写。我的学位论文《原“韵”》以中国美学中的“韵”范畴为研究对象,也是在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,后来收入《佛法与自由》一书中,算是对我的“美学岁月”的一个纪念吧!我后来发表的专题美学文章不多,但发表过五、六篇文学方面的文章,其中均渗透着我学习美学的感悟。近年来,我萌生了一个想法,那就是重新回到美学,把我平生对美和艺术的思考重新整理出来,以作为对我的“南开时代”的总结和对王老师的栽培的报答。

六、“境界总在目前”
5月28日接到王老师去世的噩耗,我于悲痛中撰写了一幅挽联:“惊闻噩耗,泪眼婆娑,人间又成别离;犹记当时,风骨清峻,境界总在目前。”这些年,我经历了许多的别离,母亲走了,父亲走了,弟弟走了,岳父走了,方老师走了,王老师如今也走了,每一次别离的背后,总有着讲不完的人生故事。王老师走了,但当年亲历的境界仍历历在目,南开园的道路、西南村的讨论、江南的园林、八里台的酒会、教室里的聆听、宿舍中的辩论、水上公园的漫步,这一切的一切组成了一幅幅情景交融的“意境”。把这些“意境”连接起来融入生命整体的究竟是什么?是“天命”?是“因缘”?是“业力”?还是“历史的必然性”?此时此刻,我想起了里尔克的《严重的时刻》,就以此诗结束本文吧!
谁此刻在世界某处哭,
无端端在世界上哭,
在哭着我。
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,
无端端在世界上笑,
在笑着我。
谁此刻在世界某处走,
无端端在世界上走,
在走向我。
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,
无端端在世界上死,
在望着我。
2025年6月4日于昆明雨花毓秀寓所
李广良
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
广瑞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